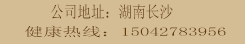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河马 > 河马的形状 >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彭树智
当前位置: 河马 > 河马的形状 >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彭树智

![]() 当前位置: 河马 > 河马的形状 >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彭树智
当前位置: 河马 > 河马的形状 >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彭树智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年02期
作者:彭树智,年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图片为编者所加,来源网络。
阿富汗在古代是东西方陆路交通上的枢纽地区。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正确地把阿富汗看作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①。它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时而是游牧世界文明的火光,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时而是希腊文化的阳光,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还夹杂有中国文化的余晖,这许多文化的光芒,都先后在阿富汗闪烁,并经过它不断打开古代闭塞之路。如果说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方式,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的阿富汗,由于民族迁移和帝国战争而成为各民族交往荟萃之地,其文化交往也呈现出异彩缤纷的诱人的图景。
一
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文化的出现。研究结果证实,阿富汗存在着石器时代的远古文化②。加兹尼省的达什基·纳乌尔发现有粗石器工具,确定为20一10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存③。此类文化遗迹还出现在阿富汗东北部的达拉伊·库尔遗址中④。那里出土的人头盖骨碎片及山羊崇拜标志的器物,为公元前一年的石器时代类型的文化遗存⑤。
人类文化本是多元的,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总要互相接触,发生交往是必然的。交往是文化的属性。远古的阿富汗,就存在着这种文化交往。在达拉伊·库尔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山羊崇拜文化现象,反映了它同克什米尔地区及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密切联系。阿富汗最早的细石器地点距今年上下,出土于阿富汗中部地区,其特征为“没有发育几何形技术、雕刻器和琢背成分的细石叶”①。这种细石器和人们在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所见到的相同。因此有人推断,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的细石器有某种联系,似乎在阿富汗具有两种细石器传统相结合的文化特征②,并证明了德日进在年提出的在新石器时代之始,北极圈邻近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世界性联系性的假说③,而且用更多实物完善了这个假说。
远古时期文化交往有明显的地域性。在阿富汗的坎大哈省发现的三个遗址(孟吉卡克、赛义德·卡拉和德赫·莫希拉·格洪达)都是土地肥沃、水量丰富的地区。这里出土的陶器图案装饰与邻近的俾路支和南伊朗早期文化有许多共同处。公元前年末至年间,南土库曼的农耕畜牧公社与阿富汗的联系当有所加强,这可能与同一些部落群体从那里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关。例如在赛义德·卡拉居民遗址发现的女性小陶俑,与南土库曼遗址中陶俑的形态相同,在彩绘陶纹装饰上也十分相似。在孟吉卡克居民遗址的文物中④,发现了类似南土库曼和伊朗北部、东部的金属装饰风格。
远古文化交往的地域性特点符合文化扩散的由近及远的规律。人们的历史交往总是从邻近地区接触开始,而文化往往就是这种接触的前哨。这主要是由于邻近地区发达文化的辐射影响所致,也与当地文化的扩散相联系,包括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阿富汗发现的许多陶器形式和装饰画的主题,可以在印度哈拉巴文化资料中找到近似的现象。除了地区邻近、可以直接接触以外,阿富汗的铜矿和青金石,对印度河谷的哈拉巴文化中心的冶金业和制陶业的供应直接相关。尤其是蓝色的青金石,在古代东方被视为最宝贵、最有魅力的珍品,早在公元前年前半期就广泛输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于埃及。当然,这是借助于多层次的商路交换①。现在得到的确切资料,当时阿富汗与印度哈拉巴文明存在着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往。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阿姆河岸发掘的肖图尔加居民遗址的下层,出土了典型的哈拉巴式陶器。虽然这只是勘探性发掘,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古代文化紧密联系的证据。肖图尔加遗址是哈拉巴文化要素在阿姆河沿岸影响的遗存。
早期文化交往过程伴随着文明区的形成,这种文明区就是阿富汗早期农耕文化的出现。公元前年正当阿富汗南部农耕文化衰落之时,北部绿洲农耕文化形成为较高水平的文化。本世纪(指20世纪)70年代苏联和阿富汗考古队在达夫列塔巴德和马扎里沙里夫之间发现了几十个农民和畜牧者的居民定居点遗址②,他们定居在五六个绿洲地带,这里出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物。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石制印章刻饰着美索不达米亚题材的双翼狮子,许多石刻雕像上也留有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艺术风格的明显印记。这些遗物经测定,约在公元前年至年初,与美索不达米亚艺术时期相符③。这里的居民可能是从邻近地区迁移而来,促进了阿富汗北部东方型文明形成的积极过程。
二
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新时期,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
从人类历史交往角度看,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既统治东方又统治西方的帝国。它以军事和政权的力量把东西方紧密地联系起来。
帝国的版图在居鲁士二世时期(约公元前一公元前年),已扩展到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从咸海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而在“王中之王”的大流士一世时期(约公元前一公元前年),帝国的统治进一步扩展到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
阿富汗的许多地区,如巴克特里亚(大夏)、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地,都归属阿契美尼德帝国,在这个跨越东西方帝国的统治之下,阿富汗成为许多民族更广泛交往的地区。这种广泛的交往和经常的接触,必然在这一时期文化交往中表现出来。
研究中亚的学者斯塔维斯基说得完全正确:“既然成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臣民,那么中亚各民族就不仅要和波斯人、米底人交往,而且也会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小亚细亚的居民进行交往。也正是这时,中亚各民族与希腊人发生了最初的接触,不仅是作为敌人在战场上相逢,而且是作为难友——被阿契美尼德王朝驱使的建筑工匠和手艺人,乃至作为官吏和波斯军队的军人而与希腊人发生交往。”①
作为中亚中心的阿富汗,就是阿契美尼德帝国通往东方的桥梁。在这个庞大帝国中,它同许多民族进行了频繁的文化交往。
首先是祆教文化的扩大。祆教或称拜火教,它同阿富汗有密切关系。该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传说中被认为诞生在阿富汗的西北部。公元前6世纪,他在阿富汗的巴尔赫创建祆教,并得到阿富汗大夏国王维斯塔帕(Vishtappa)的支持,大夏宰相娶他的小女儿为妻②。在大夏统治集团的支持下,该教盛行于阿富汗及波斯。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这样的传说: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年在阿富汗的巴尔赫附近,被入侵的游牧民族所杀害③。总之,祆教文化的中心地区是在阿富汗,其影响辐射到古波斯而成为国教。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二世敏锐地看到了祆教教义中能为帝国扩张所利用的世俗面。尤其是把最高神集中为善端的“阿胡拉·玛兹达”的智慧主宰之神和恶端的“安格拉·曼纽”的凶神,以及该教强调“哈沙特拉”(尘世主宰的强权力量)的教义,使居鲁士二世最为中意。著启的祆教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就是在居鲁士二世统治时期初次写下的。在居鲁士二世支持下,祆教迅速传遍了整个阿契美尼德帝国,形成了一个祆教文化圈。《波斯古经》中记载的社会组织(大宗法式的家庭、氏族、部族及上层地区统治机构),反映了阿富汗和东部伊朗社会面貌。毫无疑问,这是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成果。
其次是与阿富汗民族有关的游牧文化的交往。现存阿契美尼德帝国征税地区名单中,保存了有价值的古民族名称的文献资料。其中提到阿契美尼德帝国东部郡中某地的巴克基伊人,研究者认为是阿富汗部族的自称,即今日的巴什东或巴赫东④。巴克基伊人与帕米尔的游牧民族萨迦人为界。在这里发现萨迦人(即塞人)的墓葬证明,他们居住在山谷中,与巴克基伊人为邻。正如现在完全或部分包括在阿富汗地域之内的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纳及其他地区的地名所表明,这些地区在公元前年居住着操伊朗方言的居民。这些古代东伊朗的部落也就组成伊朗民族发展的基础。这些居民移居到现在的阿富汗。在巴克特里亚语与现代阿富汗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萨迦语在阿富汗语的起源中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萨迦人相当早的时候就向南迁移,而后来又和其他的游牧部落迁移的浪潮一起继续迁移。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由于阿富汗民族与萨迦人相邻而居,必然有更多的文化交往①。操东伊朗方言的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的定居居民和讲萨迦语的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阿富汗民族起源有重要意义。当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相当复杂。顺便要提到的,是巴克基伊人居住在印度河流域,他们已开辟了沿河而下通往印度文明的水上航道②。大流士一世为管理领地曾向这里派出了船队。
再次,文化交往的频繁,表现在物质条件的变化上。阿富汗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一些主要地区社会比较稳定。如巴克特里亚及其邻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波斯古经》中把灌溉农业看做神圣的事业。阿契美尼德帝国把巴比伦的灌溉技术和修建地下水系统(坎儿井)的方法在中亚推广。帝国鼓励农业发展,对建造坎儿井的人免去一定时期的赋税。阿富汗一系列著名的坎儿井(如法拉·格里什克地区)均修建于这个时期。绿洲地区城镇的兴起,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发展。从印度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贸易品:镰刀、铁铲、铁锹、犁铧等铁制工具,金银装饰品、陶器、小船、小车、马车等。这说明物质文化交往相当发达。这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保护的“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商道有直接关系。帝国势力未达到之处,商业贸易也有间接通道经阿富汗开展交往。如人们认为原产于中国的桃与杏就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传到中亚的,甘蔗、柑桔和稻米,也是这时传入伊朗的③。
商品关系的发展集中反映在货币流通方面。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帝国各郡的缴税,都规定用“塔兰特”币④支付,其中巴克特里亚每年要“塔兰特”币。当然,这是以各种不同实物提供的货币等价物,但并不排斥部分税收是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在巴克特里亚、甘德哈拉和阿拉霍西亚地区,还很少发现阿契美尼德帝国自印铸造的硬币金达利克(重8.4克)和银西克里(重5.5克),但发现了很多的希腊各城邦、首先是雅典的硬币。
东西方文化通过货币交往在阿富汗反映出来。在喀布尔发现的银币库所剩无几,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币被藏在博物馆①。当时,阿富汗的甘德哈拉也铸造地方硬币,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的银锭,上面有各种不同图案。除上述阿契美尼德、希腊和甘德哈拉的硬币之外,在阿富汗还发现了29枚十分独特的硬币。从形式上看,它们近似希腊的冲模,而根据某些图案看,又像是甘德哈拉的硬币。在这些硬币上的独创图案有:鸟、成对的山羊、象头、鬣狗等。这是文化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涵化”(acculturation,或译为“濡化”)现象②。任何两种不同文化群体发生接触时,它们之间都可能互相撷取对方的文化要素,在涵化基线上彼此吸收所需要的要素。鸟、成对的山羊、象头、鬣狗等这些固有的文化特征,被铸在希腊冲模上,就是涵化的结果。所以,有根据地推断说,这些硬币是阿富汗的卡皮萨或巴克特里亚本地所铸造③。总之,这些硬币是涵化过程中同化类型的一种表现,但也有扩散类型的要素在内。
最后,上述涵化过程最有力的证据是著名的“乌浒河(阿姆河)宝藏”。这个宝藏是塔赫季·库瓦德地方居民于年在该地的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塔赫季·库瓦德古城位于瓦赫什河与喷赤河(阿姆河上游)的交汇处,属古代的巴克特里亚。这批宝藏被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作为珍藏保存着,其中有16件人像雕塑、5件器皿、26件浮雕、53件带压模形象的薄板、16件宝石戒指和小印章、30件手镯、31件小型饰物和1枚阿契美尼德金币④。但这只是“乌浒河宝藏”的一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已经可以断定它属公元前5一公元前4世纪巴克特里亚北部某贵族或富豪家族的财宝,很能说明这个地区文化交往的特征。
“乌浒河宝藏”是巴克特里亚富贵家族聚敛财宝和审美情趣的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趣的物质见证。这批珍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种类多样,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且重要的还在于是按照阿契美尼德帝国上层统治者所崇尚的风格制作的。其中一部分是从帝国的中心地区输入的,而其余部分则是按照古波斯风格和艺术规范在巴克特里亚当地制造的。除了古波斯的宫廷艺术之外,还有古希腊手工艺工匠的作品,同时还使人感觉到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手工艺工匠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小亚细亚希腊艺术大师们的作品相当熟悉和了解。令人惊异的是,许多珍品上刻有造型刚劲活泼的动物图象,与游牧部落(所谓欧亚斯基泰草原部族兽形艺术)风格十分相似。
“乌浒河宝藏”中所反映的主体文化为古波斯文化。阿契美尼德金币上有国王的图象,头上带有典型的齿状王冠。玉髓石刻成的柱形小印章,上面刻的是波斯人战胜游牧民族的战斗场面。引人注目的是,在战场上方,祆教天神阿胡拉·玛兹达在空中飞翔,表现了祆教文化所具有的阿契美尼德王权性质。在戒指一类的珍品中,有当地巴克特里亚工匠的作品,这些戒指具有阿契美尼德的宝石雕刻艺术的独特形式——镶嵌着宝石的金戒指,其花纹虽然近似小亚细亚的宝石雕,但许多细节与它有所不同。还有一些金戒指形印章,表现了涵化的显著特征。如印章上面刻有齿状王冠的诸神,幻想中的格帕特沙赫一一长着公牛躯干、大鬍子人头的有翼怪物,古波斯柱头装饰典型的细部构件,印章用阿拉米铭文刻写的巴克特里亚女神“瓦克沙”或“罗克姗”的名字。这是阿契美尼德官方文字在巴克特里亚传播的证据。有的印章是希腊工匠的作品,其正面有掷骰子的妇女,站立着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在涵化过程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珍品中都继承了古代东方在表现人物形象时非常注意衣饰细节和表现动物形象时追求写实的传统。
三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深入亚洲腹地、远征数千公里,导致古波斯帝国的灭亡。这种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使包括中亚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文化和艺术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交往被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称为“希腊化”时期。
亚历山大远征的结果之一,是在巴克特里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希腊人为统治者的国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①,中国古籍中称之为大夏国。这个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塞琉古帝国中分离出来,之后又向印度北方扩张,历经三四代统治者,于公元前2世纪下半期,在萨迦游牧部落入侵者打击下灭亡②。
希腊文化的巨大辐射力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表现得特别强烈。亚历山大力图用军事、政治的力量积极推动当地居民的文化同化过程。他所采取的第一步是武力征服巴克特里,镇压反抗力量。第二步是笼络当地贵族力量,鼓励异族之间通婚。他本人在公元前年通过半希腊半波斯式的仪式,同巴克特里亚波斯贵族的女儿罗克珊结婚。在他的倡导下,他的许多近臣和军人都竞相仿效。第三步是经商和移民,接着便是建立新的城市。
亚历山大不遗余力贯彻着他的“世界帝国”的思想,即把所有臣民统一成一个民族的思想。于是在亚历山大的军队后面,接踵而来出现了两种文化交往的新现象:一种是尾随军队而来的希腊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商队,其中许多人迁移来后就定居下来,并同当地人通婚;另一种是一座座新兴城市在商道上拔地而起。这两种文化交往的新现象,适应贸易交往和已经发展的商品流通的趋势,为东西方文化交往增添了新的动力。
继亚历山大之后,塞琉古仍遵循“世界帝国”的思想,甚至比亚历山大更热衷于推行希腊化政策,他同粟特起义军领袖的女儿阿帕玛结婚,所生的儿子就是塞琉古王位的继承者安提俄克一世。他们二人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商城,相传塞琉古建城75座。在历法纪年上,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亚洲国家都用塞琉古国家建国的公元前年为纪元元年①。直到公元8世纪,从巴克特里亚来中国的景教徒仍沿用该历法,在《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古叙利亚文写着“时在希腊纪元年”字样。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即公元年,推到公元前年,正好是希腊纪元年。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是古代世界杰出的艺术品,二百多年来一直激动着研究者的心。这种钱币的正面通常是希腊统治者的右侧面头像,背面是保护神的形象和希腊铭文。钱币艺术是根植于亚历山大和塞琉古时代的希腊艺术,而且巴克特里亚的铸币作坊的工匠们确实有良好的希腊艺术修养。但在文化交往中,巴克特里亚的钱币艺术吸取了当地的明显不同于希腊的形式和外观,建立了一条气势庞大的钱币肖像画廊,其写实主义的水平丝毫不逊色于希腊艺术。例如,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第三代君主叶弗基捷姆时期的钱币,工匠们在刻画这位国王的个人特征上,表现了相当高的肖像艺术水平。前期的钱币上,他被表现得年轻英俊;后期的钱币上,他被刻画得老态龙钟。
希腊巴克特里王国的钱币艺术在涵化过程中走着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钱币上的希腊铭文是当时希腊语普及的表现。然而可以断定,巴克特里亚工匠们在刻这些铭文时,使用了两种文字——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的阿拉米文和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希腊文。在服饰上也可以看出这些特色。如国王德米特里钱币上的头盔是亚历山大式的希腊头像造型,而安基马赫国王钱币上却是“贝雷帽”式的无檐圆帽,这种头饰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本身生活有关。尤其是这两个国王的钱币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衣服图案,还给传统的希腊形象赫拉克勒斯加上了太阳神密拉特②的光轮。这只能用地方特性的非希腊化来解释,这些细节上的变化,是在涵化过程中的希腊传统、巴克特里亚地方特色和印度文化影响三者同在的共生现象。联想到新兴建的希腊化商城中希腊神庙同当地神庙共存的共生现象,可以认为这种现象在文化交往中带有普遍性。因此这种钱币艺术虽然是希腊趣味和成份占优势,但纯粹的希腊文化在阿富汗是不存在的。
阿富汗北部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上的大型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筑综合体的发现①,为研究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无论它是不是人们几十年来所寻觅的“大夏王城”,但它以规模宏大的希腊化城市遗址展现出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大大丰富了以前钱币学所提供的文物遗存。发掘证明,该城的创建者基涅阿斯墓址上的希腊语铭文,充分表明了这个古城遗址的希腊特色。铭文的作者为克列阿尔乔斯,他奉基涅阿斯之命,在石碑上刻下了德尔福格言的部分内容。这个格言规定了巴克特里亚希腊移民所推崇的人生各时期所应具有的品质。我参照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年5月20日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所作《阿富汗大夏遗址研究》报告及有关英文资料,将其译述如下:“少年时期学会规矩礼貌(自律);青年时期,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自制);中年时期,学会主持正义(自立);老年时期,学会助人和谘询;最后安然逝去,死而无憾。”②这种根据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时期人们的生理和道德要求而概括出来的修养规范,同儒家的“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瑜矩”,表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心态,但在文化层次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是西方希腊文化和东方波斯、印度和阿富汗文化融合的产物。阿伊哈努姆遗址的特点说明了这一事实。它一方面有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里斯和商神赫尔墨斯的铜像,以及用根廊柱建筑的科林斯式柱头的行政官邸;另方面和这些柱头一起装饰石柱的,是典型的阿契美尼德式柱础——方形阶梯式石基上的扁平的圆形基座。官邸内的平屋也不能用古希腊传统来解释,而只能说表现了东方的传统。表现阿契美尼德式建筑风格的还有用18根柱子支撑的宫殿大厅。阿伊哈努姆古城创建者基涅阿斯的“英雄墓”建筑在一个梯形台地上,这一点与伊朗帕萨尔加德著名的基尔陵墓相似。遗址中出土的大理石雕像和石膏、粘土雕像已经是日后演变为佛教造像艺术的原型,而佛教艺术造像已不是希腊式的,而是纯东方的现象了。联系到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米里德罗斯为佛教信仰者的事实,完全可以接受德拉薄所说的:“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的渠道而传到欧洲的。”①
四
公元1世纪至4世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以阿富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同汉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一起组成了强大文化交往的四重奏。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这四大帝国之间商业关系密切,文化交往频繁,世界整体性、一体化过程加快。当时有三条商道贯穿东西方,沟通着人类逐渐开放的渠道。第一条是以汉帝国的首都长安为起点,穿河西走廊和中亚,经过贵霜帝国、安息帝国的土地,到达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岸边。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横跨亚欧的驼运商路——丝绸之路。第二条是从贵霜帝国的首都到帝国的海洋门户——印度西部诸港口沿阿拉伯海,穿红海,到屋大维·奥古斯都占领的埃及。这是一条定期的航海路线,沿着这条航海路线,勇敢的东方航海者早在达·伽马之前15个世纪,便在印度洋上航行了。第三条是经过安息的草原之路,将黑海北岸希腊诸城邦与中亚联结起来。
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是游牧人的后裔②,其祖先即与汉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年,阿富汗和苏联联合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东北约5公里处的蒂亚拉·梯波遗址出土的6座墓葬③,为研究贵霜帝国的祖源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些墓葬群的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期,很可能是被大月氏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前的塞人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集团四部落之一,也许就是贵霜部落的贵族墓地。墓葬群的年代和地域,反映了塞人的历史活动情况④。
蒂亚拉·梯波遗址中的墓葬群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阿富洋与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新时期,尤其是在丝绸之路向阿富汗延伸早期的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墓葬群中出土了大约两万件珍品,最突出的是金银制品,如罗马的金币,伊朗的金银币,特别是西方式的铜制带柄镜、印度式的象牙细工梳子、罗马的琉璃小瓶。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出土了三面西汉末年的连弧文铜镜。其中有一面铜镜直径17厘米,半球形纽,圆纽座上饰以12连珠,绕以8连弧,半缘,有铭文1圈,共34字。这些文字经中国学者释读如下:
“心污(阏)结而挹(悒)愁,明知非而(不)可久,(更)囗所〔驩(欢)〕不能已,君忘忘而失志兮,爰使心央(怏)者,其不可尽行。”①
这是一则有韵的铭文诗。“久”、“已”、“志”为“之”部韵;“央”、“行”为“阳”部韵。综观汉镜铭文,分为4个类型:“吉祥语”、“商业性用语”、“神仙思想及四神观念”和“相思语”。这面汉镜的铭文属“相思语”类型中罕见者,实际上它可列入汉代诗集中的一首妇女相思的诗作。它用直白的抒情方式,表达了一位妇女愁思悱恻、怀念所欢的似水柔情。更可贵的是这面汉镜的出土环境。在蒂亚拉·梯波遗址的3号墓中,这面汉镜放置于墓主人的胸上,而墓主人的手中还握有1枚伊朗银币、脚底下放有1枚罗马皇帝提比留斯金币。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游牧贵族的陪葬拥有三个不同文化圈内的珍品于一身的豪华图景,表明了上层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和丝绸之路在阿富汗的频繁昌盛的交往情景。
贵霜帝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总特征是它在文化交往中综合性更多、融合性更强。由于阿富汗是东西方商道要冲,而这时的商道畅通、城市增多(据考证,仅巴克特里亚地区就有18个城市,移民迁来者有多万),又开通了新的商路。陆路的传统路线是通过安息到阿富汗的赫拉特城,在这里分成两条岔道:一条转弯直向南方,到达德兰吉安纳—萨迦斯坦;另一条穿过山隘和狭谷,到卡皮萨—贝格拉姆,再由此通向奥尔托斯帕纳(约相当今日的喀布尔),直达甘德哈的繁荣城市②。为了保护因贸易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商路上各驿站的距离都经过仔细测量,设有骆驼队停住地和供旅游观光名胜古迹的标志。加上原有东西交通的三条主道,为文化交往中的综合性和融合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上述阿富汗北部蒂亚拉·梯波遗址所发现的游牧贵族墓葬,也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期巴克特里亚及其周围地区的文化构成③。这座墓葬没有巨大的坟头和地表建筑物,然而陪葬品极为富丽豪华。死者身着绣满金饰品的华贵衣服,金扣环、小搭扣和匕首鞘上都用珍珠和天青石装饰着。一些艺术品带有亚洲北部游牧部落的文化风格,例如扭打在一起的、呈痛苦状的野兽雕塑;另一些则是身着马其顿式阅兵盔甲的希腊士兵的塑像;还有一件塑造着两边卧有飞龙的国王像的流垂悬饰物。这种文化现象表现了游牧民族、古希腊、伊朗、印度、中国文化的综合和融合,其深广度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贵霜王朝时期阿富汗文化一个突出的具体特征,是游牧民族草原传统的某些复活。
在发现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遗存中,草原传统似乎所存无几①。但到了贵霜时期,出土的保持欧亚兽形风格传统的许多文物。如巴克特里亚北部出土的片状青铜腰带扣环,上面有双峰骆驼与老虎搏斗的造型。还有两件兽形风格鲜明的腰带扣环:一件为金质,饰以两只麝头;一件为铜质,上有两个怪兽形象,长着鸟类的胸脯、脖颈和翅膀,而头却是两个小犄角的兽头。这种现象,可以在文化交往中的政治因素中寻找答案,想必是希腊政权崩溃后,新建的塞人和大月氏及贵霜人几代游牧人政权对祖宗的追忆,也可视为游牧民族对这一地区艺术和审美情趣影响的结果和草原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的结合②。
在上述出土文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游牧民族征服者对于制造希腊风格的物品特别偏爱。许多表现希腊化传统的当地制品,如饰有希腊神话中的智慧神雅典娜、胜利女神尼斯等形象的铜戒指,仿海豚形象的金把手等。这些工匠既熟悉草原传统、又熟悉希腊传统。他们是从哪里继承下来这些传统?有人认为是从西方的黑海北岸希腊城邦草原同胞那里继承而来,但从阿富汗在东西方交通商路的地位来看,很可能是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移民那里继承下来的。
阿富汗在贵霜时期文化交往中最重要的具体特征,是希腊化时代生气勃勃的方式、游牧民族炽热的风格与印度艺术的精致考究精神相结合。喀布尔北60公里的古城卡皮萨遗址中③,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古代艺术珍品,如汉朝的小巧玲珑的黑漆小碗,罗马的玻璃器皿,古希腊医生吉波克拉特(约公元前一公元前年)的铜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里斯及其他人物铜像。在马扎里沙西北40公里处的迪里别尔金古城遗址中,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勒达的孪生画像与贵霜王阎膏珍时期的印度教湿婆及其妻子帕尔瓦吉的画像同时出现在一个庙宇里。在许多古遗址中,都有优秀的佛教艺术文物遗存。这些都是阿富汗与东西事文化交往频繁及当时艺术情趣的实物见证。
最能清楚表明文化交往中各种交融特征的是贵霜时期在阿富汗发现的钱币。这种钱币正面为国王全身立像,背面是诸神的形象。阎膏珍时期钱币的背面为印度的湿婆神,迦腻色迦以后的钱币背面出现诸神的数目大大增加,所见者多达三十几个。这些钱币正面和背面的诸神像旁,都用“贵霜书体”(以希腊字母为基础所创造出的文字)代替了希腊文和印度文。这些神祇中,有阿富汗当地特有的神(如阿姆河之神瓦赫沙),有伊朗的神(如日光神密特拉、胜利女神瓦宁达、火神法罗),有源于美索不米亚的神(如“至高统治者”南纳尔),也有希腊神(太阳神赫利伐俄、月亮神塞勒涅、希腊化埃及的萨拉皮斯),以及印度佛教的神祇。但是所有东方神祇都是按照西方希腊模型板传统制做的①。这反映了工匠们即使在吸收当时东方文化和表达贵霜政权的愿望时,仍然利用了西方希腊文化和艺术的成果。众多神祇形象出现在贵霜钱币上,说明了这一时期阿富汗文化的多元性。这时期的阿富汗社会,是一个东西方众神汇聚的宗教文化社会;而钱币正面的统治者形象告诉我们:这种社会同样是在一个帝王集权统治下的世俗社会。
五
宗教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在宗教传播的过程中闪烁着人类文化之光。传教士们像游牧部落、各帝国武士、外交官、商人一样,在历史上匆匆过客般地东来西往,经过阿富汗这块被称为“世界征服者的舞台”,播种着文化的种子。世界上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亚欧大陆贸易线的枢纽地——阿富汗,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
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期间,佛教已经传入阿富汗,并通过阿富汗传播到希腊、埃及、叙利亚、马其顿等地②,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巴米扬的两尊大佛像、成千座佛窟以及遍及阿富汗的佛龛,生动地证明了佛教的影响。年,在坎大哈发现的石柱敕铭的具体遗址切赫·吉纳,无疑是位于古代东西方商旅必经之地。敕铭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刻写,表明希腊文化和阿契美尼德文化仍在起作用。年在坎大哈的沙达拉克和夸加之间的拉格曼地区又发现4件阿育王碑刻。这些发现,都是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的见证物。
被称为“阿育王第二”的迦腻色迦,使阿富汗变成了真正的佛教胜地。在他统治时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流派。这个流派是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中融合特征最重要的表现。它用希腊雕刻艺术的手法,来雕刻佛像和佛经的故事。佛像的头发呈波纹状,眉毛与鼻相连,笑容有所克制,希腊文化影响十分强烈。根据佛法,用艺术手法,再现了佛和菩萨沉思时的心理状态。在对其他人物的雕塑方面,工匠们则持现实主义态度。如用很大力度来雕塑有着刚毅面孔的供养人,他们有浓密的胡须,穿古罗马的短袖或无袖外衣。“苦行僧之首”的塑像,表现了一位已过中年的疲累不堪的人头像,嘴边有线条分明的皱纹,倔犟地卷起双眉,突出了其巨大的内在力量。
佛教文化通过阿富汗传入中国。据《三国志·魏志》记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统治阿富汗地区大月氏贵霜王朝派使者来中国,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有来自阿富汗的高僧支娄迦谶、支曜、支谦等人,在翻译佛经、注经、传经上,都作出了贡献。有些佛经原本就是来自阿富汗。至于中国高僧法显、玄奘,都是经过阿富汗而到印度求佛法的。尤其是玄奘来往都经过阿富汗,不仅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该地佛教文化,也有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等文化交往的记叙,成为宝贵的文化典籍。
在谈到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时,人们容易忽略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阿富汗僧侣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作用。明朝天启三年(或五年,公元或年),在西安西郊大秦寺遗址发现了上面刻着十字架和百合花图案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石碑①。这件珍贵文物是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可信史料。景教碑文下端中间,刻有一段古叙利亚文,记载了景教碑的立碑者的情况:“时在希腊纪元年,吐火罗大夏城长老米利斯之子、长安国都主教兼长老耶质蒲吉(Yesbusid,一译为叶俟布锡德)建此碑。”②吐火罗即巴克特里亚,公元4世纪起称为吐火罗斯坦。大夏城,即巴克特拉城,就是碑文中称为“王舍之城”。所以,该碑建造者耶质蒲吉就是来自阿富汗巴克特拉城,是该城主教之子。
景教为基督教一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于公元5世纪,因而又称聂斯脱利派。它在公元7世纪以后广为传播,据说信徒达百万人,有25个大主教区,个主教区。它在阿富汗的巴克特拉城设有景教主教区,上述米利斯即该区主教。一般著作中称,7世纪中期该教派由波斯传入中国和印度③,实则是由波斯经阿富汗传入中国和印度④。因此巴克特拉城是景教向东方传播的策源地。
《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的作者为波斯人景净。此人是中国北部景教教会的领袖。他是景教经典的翻译家和佛经助译。在碑文中他叙述了景教徒“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而来到长安,传播景教文化的情况。碑文中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远自王舍之城(巴克特拉),聿来中夏”的众多景教僧人的代表伊斯的德行。伊斯等僧人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传教,而且是从柘羯军入唐,帮助郭子仪军平定安史之乱,参加了收复两京之役①。由于有功于唐,伊斯被封为三品官职的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并赐紫袈裟。他“就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罸,或仍旧寺,或广法堂”,而且“当时哀矜之行,伊斯倡之,而大人君子,如郭汾阳者,皆乐效之。”伊斯不但热心于宗教事业,而且是一位杰出的阿中文化交流使者。
英人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第30章中说:“在景教徒到达唐太宗朝廷之前5年,即公元年,有一群值得注意的使者,由阿拉伯麦地那之扬布埠,乘商船越海至广州奉穆罕默德所遣,持书往见唐太宗……太宗……助之建一清真寺于广州”。这是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一说。本文则从陆上丝绸之路途经阿富汗来探讨伊斯兰教文化在阿富汗及中国的情况②。
阿拉伯人在阿富汗境内(加兹尼、赫拉特、锡斯坦、吐火罗斯坦)的征战,是在公元7世纪中期。占领赫拉特是公元年,此后逐步占领其他地区。由于当地居民的顽强反抗,最后占领要晚得多,如帕尔万、戈尔巴德和潘杰什尔到公元8世纪90年代,而坎大哈则在公元9世纪初才被征服。公元年,在巴尔赫建立了第一个清真寺。阿拉伯人征服阿富汗的过程虽然相当困难,但阿富汗的伊斯兰化过程却十分顺利。其原因正如已故的阿富汗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所说:“对于那个在当时存在着宗教、礼拜、信仰和迷信的大杂烩的阿富汗,伊斯兰教会给它带来一种新的活力,使阿富汗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伊斯兰教关于只有一个万能真主的观念,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教义,使阿富汗人的面貌完全革命化了。……不同的部落在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理想之下联合在一起了。”③
公元7世纪下半期开始,阿富汗迅速成为伊斯兰教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从此开始,结束了阿富汗的前伊斯兰教时期。公元8一9世纪,开始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对阿富汗旧有宗教和观念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改变了阿富汗社会发展的本来道路。公元9世纪至12世纪的艺术遗存中,虽然仍可看到古代传统部分,但无论在建筑艺术、装饰艺术、手工艺术各方面,都与前代艺术不同。圆形穹顶结构在公共建筑中越来越占优势。在装饰上,几何纹、植物纹、题铭性图案代替了形象化题材。
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伊斯兰教从公元年(唐永徽二年)传入中国。阿拉伯人占领赫拉为公元年。显然,此后逐渐与中国边境相接,于是,波斯人经过阿富汗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伊斯兰教。
简短的结论
关于公元9一19世纪长达千年间伊斯兰教文化在阿富汗的作用问题,拟另文阐述。这里仅就本文所论,总括几点。
(一)“交往”是一个专门的历史哲学概念。所谓“交往”是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发展的基本活动,并清楚地昭示了人类的社会性,从而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它作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同人对客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共同组成了人类历史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同动物开始区别开来的标志,“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①。在这本书中,他们多次用了“交往”(verkenr)这一概念。交往活动是与人类社会俱来、俱往的永恒不息的活动,它已为哲学界所注意,因而有“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②之说。但从人类的历史活动角度说,划分交往的类型仍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层面观察为宜。
(二)人类的文化交往是最普遍、最经常、最深层面的、也是最早的历史活动。在原始社会中,战争“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③,但它并不是人类最早的交往活动。正像上面所说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而生产活动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最早活动。只要人类产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活动,能生产物质与精神成果,就产生了文化。作为生产活动前提的个人交往,就是文化交往的最初形式。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间的交往,早在远古时就已开始。古代亚欧地区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民族迁徙,亚历山大的东征,连接欧亚大陆乃至北非的丝绸之路,进入中世纪后的十字军东侵和蒙古人的西进,其最深层面的内容都可视为人类的文化交往活动。
(三)在古代,民族迁徙和军事活动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交往④,古文化和艺术传统并不因此而死亡。事实上民族迁徙和军事活动的破坏性在深度和性质上各个地区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破坏造成的后果不久便会消失,阿富汗与东西方远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往也随之恢复,古代传统文化也有程度不等的复苏。如民族迁徙造成了阿富汗与不同地区文化的接近和民族的融合,塞人、大月氏人、嚈哒人等都在文化上与当地居民同化,形成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页的萨迦斯坦、贵霜和吐火罗斯坦文化。即以贵霜文化为例,“这一文化具有说服力地证实存在于阿富汗境域的古代文明的繁荣,同时这一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为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密切影响及广泛的文化联系和交往所决定,而交往总是确定着历史进步的总路线。”①
(四)历史上的阿富汗地区是特别值得历史学家注意之地。它曾是游牧世界文明和农耕世界文明经常冲突和彼此吸收涵化的临界地区,也是各强大邻国和民族争夺的前沿地区。更重要的,它在古代世界史上又是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原始宗教、祆教、希腊宗教、佛教、印度教直到伊斯兰教等宗教辐射传播的交汇地区。阿富汗不但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有特殊的民族构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因而必然与四邻有不同的文化形态。阿富汗古代文化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移民文化的外来特征;第二,东西方各时期主导文化的开放特征;第三,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征;第四,逐步形成与当地传统结合的统一文化的趋向性特征。
(五)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史,把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②,把交往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交往和交换综合考察,就会更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面貌。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精神交往。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精神交往的基础。从某种程度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开闭塞状态、走向世界的交往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将交往扩展到周围地区乃至各时代力所能及的心目中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③的命题,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带有本质意义的转折点,揭示了人类普遍交往的扩展对文化积累和进化的重要性。在“世界历史”尚未确立时,人类文化的互动,只局限于各民族及狭隘的地域内。只有当“世界历史”出现并不断深化后,人类文化的互动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当代出现的现代化潮流,就是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共生、共存和同步发展而来的历史趋势。
彭树智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hemazx.com/ahsc/3361.html